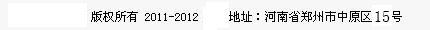摘要:在莫言小说中,常见由动物精灵、鬼魂、妖魅化的人物等构成的诡谲现象,形成了已为评论界多有论及的怪诞性、魔幻性、梦幻性、幻觉性、巫幻性等特色。这类特色,虽与马尔克斯、蒲松龄等人的影响有关,但从整体上来看,是中国乡村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以及地域文化对莫言综合影响的结果,亦与莫言敏感于奇异事物的心理机制相关。莫言小说中多见的“邪魔鬼祟”,不仅突出体现了作者的民间文化视野,且通过这一视野,深刻表现了人性反思、人类生态反思及人类现代文明反思等世界文学精神。
关键词:莫言小说民间文化诡谲现象邪魔鬼祟
作者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济南)。
在莫言小说中,常见高密民间口头所说的“邪魔鬼祟之类诡谲现象,正是这类现象,体现了莫言突出的民间文化视野,且作为主导性元素,构成了其作品已为评论界多有论及的怪诞性、魔幻性、梦幻性、幻觉性、巫幻性之类特色。因而由“邪魔鬼祟”之类的情节与形象入手,或可更有助于看出莫言小说的独特旨趣与文学价值。
1莫言小说中的“邪魔鬼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动物精灵。在中国民间传说中,不论什么动物,都可能神通广大、成精成怪。在莫言小说中,便常见这类动物精灵。如《弃婴》中,胶县南乡一个老头清晨捡粪时碰到了一只断腿的狐狸,便背回家养着。在部队当营长的儿子回家探亲时,开枪打死了狐狸,结果,包好的饺子下锅后,捞上来全成了驴屎蛋子。夜里,家里所有的门窗一齐乱响,实在没法子了,只好给狐狸出了大殡,才得以安宁。《爆炸》的中“姑姑”,曾亲眼看见过狐狸炼丹:一颗碗大的火球在眼前慢慢升起、落下,像两个孩子在抛球,一只狐狸露了一下相,紧接着一溜烟走了。在长篇小说《蛙》中,莫言这样描写了“姑姑”在一个月夜回家经过一片苇塘时,突遭群蛙袭击的经历:青蛙们,愤怒地鸣叫着从四面八方涌上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团团围住了姑姑,姑姑一边嚎叫一边奔跑,但身后那些紧紧追逼的青蛙却难以摆脱,身上穿的一条肥大的黑色绸裙,竟被青蛙一条一条地撕去了。在《蝗虫奇谈》中,莫言展现了神蚂蚱出土的可怕景观:在嘭嘭的爆炸声里,蚂蚱们从泥土中蜂拥而出,一瞬间就遮天蔽日了,将庄稼叶子甚至连草叶儿都吃没了,百姓们只好无奈地跪求蚂蚱神开恩。另如《草鞋窨子》中,小轱辘子说他亲眼见过,或是他爹亲眼见过的,像人一样站在墙头上、会说人话的“话皮子”,等等。
第二类,鬼魂。按科学的说法,世上是没什么鬼魂的,人死如灯灭,死后就一切都不存在了,而在莫言小说中,则“鬼魂”时显,且情态各异,来路有别。其中,有的是相识之人死后变成的“熟鬼”,如《奇遇》中,回家探亲的“我”在村头遇见了邻居赵三大爷,说了话,敬了烟,赵三大爷还让“我”捎一烟袋嘴给父亲抵还5元钱的债务。回家后得知,赵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这种情况,用高密民间的说法叫作“活见鬼”。有的是来路不明的“野鬼”,如《草鞋窨子》中五叔所讲的村里的老光棍家中的鬼:门圣武家住在“阴宅”,他每天夜里喝醉酒回家,就看到有一个穿一身红缎子的女人在门口站着等他,还能听到女人的喘气声,门圣武想扑上去搂她,一扑,必定撞到门上,那女人就在他身后叽叽嘎嘎地笑。又有民间所说的“起尸鬼”,如在《筑路》中,曾是盗墓贼的代理队长杨六九,夜盗乔家闺女的坟墓时,那深红褂子如血染,蓬头散发的“起尸鬼”跳出坟墓,凄厉地叫喊着,紧追杨六九不放。
第三类,妖魅化的人物,具体又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由动物精灵变成的人。如《夜渔》中那位面若银盆,头发很长,香气扑鼻,满脸微笑,在月光中亭亭玉立,帮“我”捉了两麻袋大螃蟹,令“我”怀疑是神、是仙、是狐狸精,但却遭她否认的年轻女子;《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那位幽灵一般无法摆脱,跟踪着上尉军人王四不放,直至其家,并于王四新婚次日与之拥吻在一起死去的女人,按王四自己的判断:“这女人是狐狸变成的。她是一匹狐狸精。”
二是常人因精灵附体而成了妖怪。如《丰乳肥臀》中成了“鸟仙”的三姐,能纵身一跃,跳上树梢,又能轻盈地从一棵树跳到梧桐树上,且能为人看病;《翱翔》中的燕燕,因不甘心嫁给一脸大麻子的老光棍洪喜,逃出洞房之后,竟像一只蝴蝶,扇动着胳膊,飞到了村东老墓田的松林里,村人赶来围追堵截时,她能在树冠间飞来飞去;《酒国》中的丑八怪余一尺,像李一斗所说的,是个“半神半鬼的家伙”,能一跃飞到天花板上,在天花板上轻松愉快地爬行,像一只壁虎。
三是现实的人具有了动物体征,或径直变成了动物。如《屠户的女儿》中的香妞儿,生有两条像鱼尾巴一样的腿,这决定了她遭到人类世界排斥的命运;在《幽默与趣味》中,身为大学教师,处于各种压力与鄙视之中的王三,只在一分钟之内,就变成了一只绿毛青脸的雄性猿猴,两腿间缓慢地长出了一条粗大油滑的尾巴,一直触到地面上。因为家里有了一只猴子,戴红袖标的老太太们找上门来,妻子汪小梅不堪其扰,只好带着成为猴子的丈夫远走他乡。
四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其不无魔性,亦给人“邪魔鬼祟”之感。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位有着特异功能的小黑孩,用莫言自己的说法,那就是“一个精灵,他与我一起成长,并伴随着我走遍天下,他是我的保护神。”另如《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生死疲劳》中的蓝千岁等,都有着非同常人的感知能力。在莫言小说中,这类“精灵”式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值得进行专题研究的人物谱系。
上述不同形态的“邪魔鬼祟”,或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生存准则演绎着与人类世界之间的情仇恩怨,或以奇行异秉呈现着浩渺宇宙中生命现象的斑斓与奇异。正是这样一个出自作家民间文化视野的“邪魔鬼祟”世界,强化了莫言小说独具个性的审美旨趣与诱人玄思的艺术魅力。
02通常的看法是,莫言小说中的诡谲现象与神秘色调,主要是受到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莫言在《两座灼热的高炉》、《学习蒲松龄》等文章中亦曾有过如是表白。但从莫言的人生历程、生活背景与创作历程来看,其创作特色的形成,除了受马尔克斯与蒲松龄等中外作家的影响之外,亦另有其他多方面的重要根源。
其一,中国乡村的民间传说与民间故事的影响。莫言多次讲过,他是听着爷爷、奶奶、大爷爷及乡亲们的故事长大的,而那些故事,亦多是神鬼狐怪之类。莫言说:“在他们的故事里,死人与活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动物、植物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许多物品,譬如一把扫地的笤帚,一根头发,一颗脱落的牙齿,都可以借助某种机会成为精灵。在他们的故事里,死去的人其实并没有远去,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当然也监督着我们。”莫言曾经慨叹,当时他听到的许多故事,比自己在小说中写出来的还要精彩,如大爷爷讲过的遭到一个变为美女的白鳝精诱惑的故事等。莫言透露,仅现在还能记得起来的这类故事就有三百多个,每个稍加改造就是一篇不错的小说,而自己写出来的还不到五十个。可见,在描写“邪魔鬼祟”方面,最早影响了莫言的不是蒲松龄,而是他的爷爷、奶奶,尤其是他那位身为乡村医生,经多见广,擅长即兴编造神奇故事的大爷爷。
其二,故乡地域文化的影响。据方志记载,莫言的故乡,临近大海的高密,至明清时代,尚人烟稀少,湖泊漫布。至20世纪60年代,犹多见原始状态的大片水洼、野草丛生的沼泽。历史上的高密,又曾是奉行姜太公“因俗简礼”治国方略的齐国腹地。或许正是缘于自然之谜的濡染与文化遗绪的影响,在高密地域文化中,有着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主流文化不同,且一直兴盛不衰的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以及对术士巫觋的世俗信仰等。莫言在《猫事荟萃》中,就曾这样写到过自己对高密乡村的童年印象:“狐狸、黄鼠狼、刺猬,都被乡民敬做神明,除了极个别的只管当世不管来世的醉鬼闲汉,敢打杀这些动物食肉卖皮,正经人谁也不敢动它们的毛梢。”据笔者所知,虽中经移风易俗的长期宣传,以及“文革”期间的清理批判,但直到现在,在高密乡间的不少百姓家中,还像《丰乳肥臀》中所写的上官家供奉“鸟仙”那样,暗中供奉着某类动物的“仙位”。这样一种当属原始信仰遗绪的诡异地域文化氛围,无疑为莫言小说中的“邪魔鬼祟”提供了丰厚的故事土壤与意象资源。
其三,莫言自己的心理机制。或许与自幼即沉浸于鬼怪故事氛围,以及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染有关,莫言自身就有着对自然事物的超常敏感,如他自己曾这样坦陈:“我必须承认少时听过的鬼怪故事对我产生的深刻影响,它培养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它影响了我感受世界的方式。童年的我是被恐怖感紧紧攫住的。我独自一人站在一片高粱地边上时,听到风把高粱叶子吹得飒飒作响,往往周身发冷,头皮发炸,那些挥舞着叶片的高粱,宛若一群张牙舞爪的生灵,对着我扑过来,于是我便怪叫着逃跑了。一条河流,一棵老树,一座坟墓,都能使我感到恐惧,至于究竟怕什么,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据阿城讲:“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辽宁大连,他讲起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对于这类奇异经历,与其说是莫言出于小说创作习惯的虚构,毋宁说是莫言确乎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敏感于怪异事物的心理机制,其小说中频频可见的“邪魔鬼祟”,恐亦与此敏感的心理机制不无关联。
笔者以为,正是上述几个方面,更为根本性地决定了莫言作品中突出存在的诡谲现象。至于蒲松龄与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或许主要体现在为莫言的创作提供了叙事视角、故事虚构、奇异想象等方面的借鉴,激励并坚定了其创作个性的生成。对于其创作经历,以及早期不少作品中就已突出存在的“邪魔鬼祟”现象,莫言自己如下的说法应当更为切实:刚开始创作,就“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跟蒲松龄先生同样的道路”,后来,才“自觉地以蒲松龄先生作为自己的榜样来进行创作。”“成了作家之后,我开始读他的书,我发现书上的许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说过。我不知道是蒲松龄听了我的祖先们讲述的故事写成了他的书,还是我的祖先们看了他的书后才开始讲故事。现在我当然明白了他的书与我听说过的故事之间的关系。”由“不自觉”到后来“自觉”学习蒲松龄的创作历程可知,莫言小说中的诡谲现象及创作特征的形成,并非始源于蒲松龄,而是在接触蒲松龄之前。此外,莫言还曾这样指出过蒲松龄的创作缺陷:“他也被世间的功名利禄的绳索紧紧地捆绑,他也有许许多多的个人生活的不如意,而且这些不如意也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流露,而且这种不如意,个人的一些思想感情也限制了他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具有历史的局限性。”这样明确的理性认识,决定了宣称蒲松龄是自己导师的莫言,必会在创作中尽力超越蒲松龄。
对于马尔克斯,莫言也这样讲过:“当我第一次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同时也惋惜不已,这些奇情异景,只能用别的方式写出,而不能用魔幻的方式表现了。”他同时还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像马尔克斯那样,“继续迷恋长翅膀老头、坐床单升天之类鬼奇细节,我就死了。”可见,自接触马尔克斯之初,莫言也已在设法拉开与马尔克斯的距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评价莫言创作特征的“hallucinatoryrealism”一语,曾被中文媒体译为“魔幻现实主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谢尔·埃斯普马克教授来中国访问时曾专门做过纠正,明确指出:“我们的颁奖词里没有提到过魔幻这个词。我们用的词是‘hallucinatoryrealism’(幻觉现实主义),而避免使用‘magic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过时了。莫言获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现实的描写,他是现实主义描写的魔法师———他观察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和现代,这是他的特色和创新。”用“魔幻现实主义”来概括莫言,“这会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马尔克斯或者福克纳,好像莫言只是在模仿别人,这会贬低他的价值。我们的颁奖词更有幻觉、幻想的意味,他的想象力丰富,扎根于中国传统的说书艺术,这是他超过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地方。”中国文学评论家吴义勤亦曾以“中国式的魔幻主义”概括莫言的创作。这类评价,无疑更为符合莫言创作的实际。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莫言与蒲松龄、马尔克斯的作品细加比较,就会看出,莫言虽深受后二者的激励与影响,但莫言之所以为莫言,终归是因其创作追求与作品自有不同之处。蒲松龄重在“刺贪刺虐”的创作主旨,马尔克斯通过神话般的历史叙述,重在揭示20世纪上半叶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所处的封闭、落后、腐败和独裁的社会氛围,令其作品更多一些道德寓言或政治寓言的意味,而莫言笔下的“邪魔鬼祟”则别有旨趣,更富于人性反思、生态反思、现代文明反思等方面的意蕴。蒲松龄记录他人故事的创作方式,决定了相对于故事本身而言,作者一直是冷静的“他者”,因而其作品,总给人以民间百姓所谓“扒瞎话”的印象,故有王渔洋“姑妄言之姑听之”(《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之论。而莫言小说中的许多“邪魔鬼祟”现象,则虚实莫测,真假难辨,更具本原性的神秘意味。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同样有别于可信的现实,马尔克斯自己的说法是:“在我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并透露《百年孤独》中的俏姑娘扯着床单飞上天空,是缘于有一位老太太某天早晨发现她的孙女逃跑了,为了掩盖事情真相,逢人便说她的孙女飞到天上去了。据此可知,马尔克斯所说的“现实的基础”并不等于“现实”本身,他笔下的那位俏姑娘飞上天,只是基于一位老太太的“说”而已,并无真实性可言。另如他在《一个长翅膀的老人》中所写的佩拉约突然发现在自己院子里的泥水中出现了一位长翅膀的“天使”,还有那位因违背父母之命而于一道闪电中变成了意大利狼蛛的少女等,也给人难以置信之感。而在莫言的小说中,不少“邪魔鬼祟”现象,让人感觉都是真实存在着的。如《夜渔》中那位帮“我”捉螃蟹的神仙一般的女子,虽似梦幻,但作者分明又通过特定的设计让人相信绝非梦幻。小说中写到,第二天人们找到“我”时,身旁确实有两麻袋螃蟹。那个神秘的女人告诉过“我”:“二十五年后,在东南方向的一个大海岛上,你我还有一面之交”。果然,二十五年后,在新加坡的一家大商场里,“我”在跟随朋友为女儿买衣服时,遇到了一位很像是当年那位女子的少妇,对“我”妩媚一笑,随即就消逝不见了。这类真假难辨、似梦非梦的情节与场景,就既不同于蒲松龄的“姑妄言之”,也不同于马尔克斯主要基于“现实基础”的魔幻。
03从中外文学史来看,“邪魔鬼祟”之类诡谲现象,本身并无新奇之处。除了各国早就有的古代神话传说之外,在后来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亦常常可以看到。在我国,除以花妖狐魅为主要题材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外,另有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唐代牛僧孺的《幽怪录》,宋代徐铉的《稽神录》,明代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诸多志怪志魔之作,在《红楼梦》中,亦不乏王熙凤在大观园里看见了死去的秦可卿的幽魂之类灵异事件。在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多次出现了老国王的鬼魂,瑞典现代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的一部著名剧作叫《鬼魂奏鸣曲》。或许与崇尚科学的现代启蒙思潮相关,“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除徐訏等个别作家之外,在主流文学界,已少见对神秘现象的描写了。在年以来的大陆文学中,由于“唯心主义”、“封建迷信”之类的意识形态禁忌,文艺作品中的神秘现象就更是绝迹了。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神秘现象又重现于文学作品,且呈现出日渐显赫之势,构成了有待深入研究的文学转型景观之一。如在被视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树王》、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等作品中,已弥漫着浓郁的神秘色彩。在此后陆续出现的阿来的《尘埃落定》中,作为主人公的那位傻子,就是一位未卜先知的精灵。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有这样的情节:金祥在去南山背鏊子时,路遇“黑煞”,回家后竟一病不起死去了。牛杆的老婆庆余,亲眼看见了死去的丈夫牛杆和村里的另一位死者老转儿的鬼魂在村头争斗,亲耳听见了两个鬼魂的吵闹声。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在伊万的葬礼上,突然出现了两个身穿素白衣服,无人认识,自称是伊万干女儿的俊俏姑娘,葬礼结束之后,便奇迹般地从墓地消失了,没人知道她们是怎么来的,也没人看见她们是怎么消失的。据有着敏锐直觉的“我”姑姑依芙琳的说法,那一定是伊万年轻时在山中放过的那对白狐狸,前来报答伊万的不杀之恩。在基本属于传统写实性作品的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亦有长工鹿三被田小娥鬼魂缠身的情节。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那位能卜善卦的朱先生被作者写成“白鹿”精灵的化身,他去世时,朱白氏即亲眼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然而去了。在纪实性很强、被称为“新体验小说”的毕淑敏的《预约死亡》中,亦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在一个中秋节的夜晚,医院的护士小白和齐大夫,亲眼看见一医院的院子里欢聚。这样一种趋向,让人感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向传统神秘气息回归的倾向。由此可见,莫言小说中的“邪魔鬼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在新时期以来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创作视野得以拓展的产物。与其他作家相比,莫言又有以下不同。
在其他作家笔下,神秘之事常常不过是一鳞半爪,仅见于作品局部,或偶尔为之,尚未构成整体性的创作特征,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艺术世界。而在莫言这里,其诡谲现象,不仅漫散于许多作品,且涉及诸种形态的鬼魂、妖魅化人物及众多的动物精灵,从而构成了一个堪与正常的人类世界比并而存的“邪魔鬼祟”世界。莫言小说《罪过》中的“三爷爷”曾这样说过:“地球上不止一个文明世界,鱼鳖虾蟹、飞禽走兽,都有自己的王国。”其中透露出来的,似正是莫言对大自然的观感与理解。他正是常常以此为主体视角,并据此展开想象,从而创造出了一个神秘世界。正是缘于这样一个世界,莫言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家,而呈现出以玄秘莫测为突出特征的创作个性。
莫言有着真正的民间立场与民间文化视野。年10月,莫言在苏州大学题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一次演讲中,申明过他的“民间写作”观,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非“为老百姓写作”。“作为老百姓写作”,“就要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莫言说自己采取的策略就是“避开热闹的地方,回到民间、回到传统、回到边缘地带。”与理性化、纯粹化了的精英文化相比,保留了古代遗风、体现为世俗信仰、未经精英文化过滤的“邪魔鬼祟”文化,无疑更具民间文化品性。莫言正是通过回归老百姓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视角,抓住为正宗文化漠视的边缘文化现象,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在更深层次上接通了民间审美意识与民间文化心理,形成了更具民族性与原生态性的创作风范。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崛起于中国文坛的莫言,其创作自然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涌进的西方现代先锋思潮的影响,但因其能始终立足于以“高密东北乡”为标识的中国民间大地,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汲取着民间传统文化与艺术智慧的营养,也就使其作品整体上体现出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荒诞离奇、波诡云谲的当代性,而深隐着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经验。诚如雷达这样评价的:“在莫言身上,确也存在过先锋性与本土性、实验性与民族化的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且时有侧重,但最终,莫言走的是以民族化、本土化、民间化,以继承与转化中国审美传统为根本的创作路线。”
04在我国,存在敬畏“邪魔鬼祟”现象的地域,当然绝非仅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自幼就深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熏染的作家,也不止莫言,而莫言何以对“邪魔鬼祟”的世界殊为感兴趣?其作品又有何独特意义?对此,虽已有诸多研究成果论及,但大多是从“荒诞叙事”、“魔幻风格”之类层面着眼。就笔者所见,值得重视的是李洁非早在年就曾发表过的看法:“莫言的小说明显地不是民间狐仙鬼怪故事的重复。不错,他用了不少这类题材和意象,但传奇色彩在莫言作品里只是一种包装,而非目的——他的目的在于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李洁非结合作品个案,分析论及的莫言这类小说中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主要有:“对人的某种生命处境的领悟”、“对理想主义既怀恋又悲哀的心情”等。我们结合莫言后来不断发表的大量作品,从整体上进一步予以分析,会意识到,莫言这类小说中的“意识形态与世界观”,更集中、更明确,也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人性、对人类生态环境以及对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等方面。
在莫言小说中,实际上可见两种不同形态、不同性质的“邪魔鬼祟”:一是由动物精灵、鬼魂之类构成的“邪魔鬼祟”,二是人类世界中的“邪魔鬼祟”。
前一类“邪魔鬼祟”给我们的感觉是:虽令人生畏,又不乏可敬可爱、可亲可近之处。它们或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其乐,如《爆炸》中的狐狸们在夜色中炼丹,《罪过》中的鳖精化身白胡子老头,在月下的水面上对酌;或期望着与人类和平共处,如《夜渔》中那位帮“我”捉螃蟹的神秘女子等。即使有害于人者,也多是因人类的作恶在先,如《罪过》中,是三爷先对着鳖精们开了枪,小福子才莫名其妙地淹死在鳖湾里;《筑路》中的“起尸鬼”追赶杨六九,是因杨六九前来盗墓。尤为令人感动的是,“邪魔鬼祟”们不乏光明磊落、正义善良乃至以德报怨之类的高尚之举。如《红高粱》第五章《狗皮》中那条差点被老耿开枪击中的红毛老狐狸,当老耿被日本兵刺倒在地,血流如注,奄奄一息时,竟从芦苇丛里跑过来,为老耿舔疗伤口,救了老耿一命。如《翱翔》中,似有某一隐秘的精灵,附体燕燕,助其远走高飞,以抗拒因换亲而被迫嫁给老光棍的不幸婚姻。即如鬼魂,给人的感觉亦如同《奇遇》中的“我”所体悟到的:“并不如传说中那般可怕,他和蔼可亲,他死不赖账”。
与由动物精灵、鬼魂之类构成的“邪魔鬼祟”相比,真正可怕的倒是人类世界中的“邪魔鬼祟”。如在《生蹼的祖先们》中,“我儿子”“青狗儿”就是一个可怕的妖孽:他喜欢折磨小动物,他曾凶狠地手撕活生生的小鸡,他看到羊羔就咯咯吱吱磨牙齿,会钻空子将羊羔咬死;他有一种奇异能力,能让院子里的草垛莫名其妙地起火,并伴随发出一声巨响。另如《天堂蒜薹之歌》中,那位把一根生满硬刺的树棍子戳进羔羊肛门的治保主任,《檀香刑》中那位冷酷的以杀人技巧为荣耀的赵甲等,也都“邪魔”得可怕。尤其令人惊骇的是,《酒国》中出现的李一斗的那位岳母,虽披着大学副教授的现代文明的亮丽外衣,实乃一令人毛骨悚然的“邪魔鬼祟”。她这样向学生讲授烹饪婴儿的过程:“我们即将宰杀、烹制的婴儿其实并不是人,它们仅仅是一些根据严格的、两厢情愿的合同,为满足发展经济、繁荣酒国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人形小兽。它们在本质上与这些游弋在水柜里待宰的鸭嘴兽是一样的,大家请放宽心,不要胡思乱想,你们要在心里一千遍、一万遍地念叨着:它们不是人,它们是人形小兽。”她进而这样操刀讲解演示了宰杀婴儿的要领:第一步,攥住肉孩的小脚,从脚底切口,暴露出动脉血管之后,再切断引流;第二步,要尽可能完整地取出内脏;第三步,用70℃的水,屠戮掉他的毛发。那些慕名前来吃过酒国婴儿宴的政要、尊贵的国际友人、大名鼎鼎的艺术家、社会名流等,也让人感到不无“魔性”。即如《蛙》中那位本为“人间天使”的姑姑,也“魔性”得可怕:她在将近万名婴儿接生到人间的同时,也冷酷无情地用王胆的丈夫所说的“魔爪”扼杀了无数正在孕育中的生命,且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因此导致她晚年陷入了“悔罪”的惶恐之中。正是面对人类世界的这样一种“邪魔鬼祟”,我们不能不深刻共鸣于《弃婴》中的“我”与《罪过》中的大福子、三爷爷曾经发出的如下慨叹:“人类在宇宙上的位置,比蚂蚁能优越多少呢?到处都是恐怖,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欺骗、谎言、尔虞我诈,连葵花地里都藏匿着红色的婴孩”;“世界上最可怕最残酷的东西是人的良心,这个形状如红薯,味道如臭鱼,颜色如蜂蜜的玩意儿委实是破坏世界秩序的罪魁祸首”;“人其实比鱼鳖虾蟹高明不了多少,低级人不如高级鳖”。
或许与“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儒教有关,在我们的文化中更多的是对于人性的肯定与赞美,缺乏西方文化中那样一种对人之原罪的认识与警惕,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文学作品的人性深度。正是由此着眼,我们可进而看出莫言“邪魔鬼祟”视角的价值,也会更为深刻地理解莫言许多作品的内涵。比如关于《檀香刑》,莫言曾自述道:“写作这本书时,我经常沉浸在悲痛的深渊里难以自拔。我经常想: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同类施以如此残忍的酷刑呢?是谁给了他这样的残害同类的权力呢?许多看上去善良的人,为什么也会像欣赏戏剧一样,去观赏这些惨绝人寰的执刑场面呢?”“是什么力量,使同是上帝羽翼庇护下的人类,干出来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这种暴行,并不因为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昌明而消失。”透过对人类自身暴行的痛苦体悟,可使我们更为正确地意识到,这部作品,绝非如有人肤浅指责的那样,是在渲染血腥与暴力,而是基于对复杂的审视,揭示了人类应予自省的自身的“邪魔鬼祟”性。在《我们的恐惧与希望》一文中,莫言曾更为痛切地指出,比鬼更可怕的是丧尽天良的人,“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在年的一次讲演中,莫言还这样总结了自己的创作追求:“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显然,正是基于“把自己当罪人写”的“自审”意识,在长篇小说《蛙》中,莫言着力揭示了以自己为“原型”的蝌蚪这个人物的自私心理与阴暗欲望。据此,我们进而可以看出莫言对人性反思的眼光。
在现代文明视野中,精灵鬼怪与蛮荒、落后、迷信之类不无关联,但生命现象原本就是神奇、复杂、玄秘莫测的。在自然世界中,人类的生命也原本更为充盈、更为活跃、更为多姿多彩。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气象万千的自然也遭到了漫无节制的侵蚀,人类的生命空间遭到了严酷的挤压。对此,许多思想家、科学家不乏忧思,形成以保护物种与自然环境为主旨的生态文明思潮。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莫言,小说中写及的“邪魔鬼祟”,亦正含有这样一种与世界性时代思潮相通的意旨。如在中篇小说《爆炸》中,当“我”对姑姑说希望能碰到一次狐狸炼丹,也好开开眼时,姑姑不无忧愤地说:“绝对不可能了,现如今人太多了,鼻子里眼里都是人,人多地面窄,人多心眼黑,山猫野兽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到哪里去炼丹!”在《屠户的女儿》中,妈妈告诉香妞儿,当年的黑松树林子中,夜间的鬼火就像小毛人提着小灯笼,在坟地里飞来飞去;很多白色的夜猫子,哇哇地叫;一些穿小红袄的小毛人,拖着一根毛谷穗一样的大尾巴,在树林里藏猫猫、过家家。后来来了一些人,将坟墓扒了,林子砍了,这风景也就没了。这很令香妞儿失望,她产生的念头是:“我恨那些人,他们把鬼火撵跑了;他们毁了小毛人的家,更毁了妈妈看过的风景。”在姑姑、香妞儿等人物对“邪魔鬼祟”世界的向往与依恋中,流露出的亦是莫言对原本绚丽多彩的生命世界与生态环境惨遭毁损的忧思。
面对生态破坏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当今世界上有不少思想家、科学家,已从根本上反思科学以及相关的现代文明,注重对自然界中的神秘现象的研究。如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高津等人已指出的:“特别是在宇宙学家中,神秘论又重新受到崇尚。即便是某些物理学家和科普工作者也认为,在灵学和量子物理学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就曾这样明确说过:“我把科学和神秘主义看成是人类精神的互补体现,一种是理性的能力,一种是直觉的能力。它们是不同的,又是互补的。……两者都是需要的,并且只有相互补充才能更完整地理解世界。”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大卫·格里芬甚至据此提出了“科学的返魅”等主张。莫言小说中的“邪魔鬼祟”视角,分明是与上述反思人类文明的时代思潮暗合的。就其创作思维与具体作品来看,诚如李洁非曾敏锐指出的:“莫言属于那种习惯于用小说向世界发问的人。他一般不承认世界业已有什么固定的现实,所以他也不喜欢仅仅呈现这种固定的现实”,并缘此而形成了莫言小说的独特审美个性,这就是:“大多数小说使人读后明白了世界是怎么回事,而莫言的小说却使人读后对世界感到神秘费解起来”。而正是这类特征,决定了莫言小说与一般鬼怪小说、魔幻小说的不同,即其中体现出来的既非民间故事中常见的重在道德说教的“寓言”性,亦非《西游记》之类传统神魔小说所体现的“神话”性,又非蒲松龄那样重在“刺贪刺虐”、马尔克斯式那样重在揭示社会现实腐败落后的批判性,而是注重通过对具有本原神秘特征的“邪魔鬼祟”现象的审视与描写,从文化哲学层面上反思人类文明视野的偏狭。
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莫言笔下的“邪魔鬼祟”亦别具文学本身的意义。文学不是科学,不能像科学那样,旨在逻辑化、实证化、理性化地说明世界,而是要表现世界的丰富与复杂,而“邪魔鬼祟”原本就是大千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对此视角的重视,不仅可以修复长期以来我们所尊崇的太过理性化、科学化的现实主义创作观的罅漏,也扩充了自“五四”以来,为“理性科学”所框拘了的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想象空间。
在莫言笔下,荒诞不经、诡谲离奇、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与审美空间的“邪魔鬼祟”现象,虽取之于中国民间,深隐着民族文化心理与本土审美经验,但正是基于人性反思、人类生态反思及人类现代文明反思之类深阔博大的文化视野,才构成了其作品中超民间、超本土、超国度及超时代性的世界文学精神,从而成就了中国的莫言,又是世界的莫言。
〔责任编辑:马涛〕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年第1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