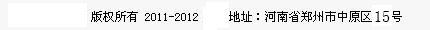参与编撰《川菜烹饪事典》
作者:张中尤
年,四川省商业厅决定组织编撰《川菜烹饪事典》,指定四川省蔬菜饮食服务公司落实这件事。那时成都和重庆还没有分开,两边都派人参加。编写人员有从事饮食文化研究的,有专业厨师,也有一些餐饮行业的管理人员。重庆方面有侯汉初、曾亚光等老师傅,以及重庆市中区饮食服务公司的科长阎文俊、张国柱、蔡雄师傅等,成都这边有张富儒、蒋荣贵、刘建成、熊四智、胡廉泉、四川烹饪专科学校的老师罗长松、成蜀良和多位四川省各地市的专业人员等。此外,四川省蔬菜饮食服务公司、四川省饮食服务技工学校、成都市饮食公司、重庆市饮食服务公司、重庆市市中区饮食服务公司也派人参与进来,阵势搞得比较大,是“文革”结束后川菜行业一次空前的文化整理工程。现在回头来看,那时的上级领导确实很有远见,也很有魄力,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那年我在努力餐当厨师长,是西城区饮食公司唯一派去参与这项工程的人。接到组织调令后,我既紧张又兴奋,深感责任重大,决心加倍努力,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编辑部办公室设在新都区新繁镇一家由旧时的公馆改建的国营旅馆内。我们每周休息一天,周六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又去,足足待了一个多月。当时交通不方便,要到营门口的西门车站搭长途汽车,路上要一个多小时。
编撰工作开始时,先让每人填了一张表,以便了解各自熟悉的产品和类别,再根据这个来分配工作。我参与编撰的,主要是林家治、李德明两位师傅教授的一些菜肴和点心,其中有家常鱼翅、红烧鱼唇、双味鱼条、烧什锦、凤尾酥、鸳鸯叶儿粑、层层酥鲜花饼、玉兔米饺等。平时,编撰人员各写各的,需要集中起来讨论问题时才坐到一起。
那个年代,关于川菜的书籍、资料极其缺乏,我主要是靠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笔记,再加上师傅口传心授时的回忆来归纳整理。每道菜都要按照写作规范,介绍味型、配料、操作要点,文字要准确精炼,还要通俗易懂,这就需要反复斟酌、修改、打磨。该书是烹饪工具书,别人是要拿来学习和操作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要绝对保证编撰质量,所以谁也不敢马虎,力求准确无误。
编撰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比如“味型”,川菜行业早已有了共识,大家一直在用,虽然各地在细节上有些差异,但在概念上没多大的争议,标准也差不多,例如麻辣味、红油味、椒麻味、怪味、煳辣味、鱼香味等,味道感觉基本一致,整理时也就容易统一意见。
有些菜,重庆和成都的制作方法不太一样。比如干烧,成都的干烧鱼与重庆的干烧鱼是有区别的。成都的用芽菜和臊子(碎肉),一般用草鱼来烧;重庆的是用肥瘦肉丁、冬笋丁、岩鲤来烧。重庆有大江大河,岩鲤是那儿特有的江鲜。整理时我们保留了菜肴的特色,把干烧岩鲤以及红烧牛头方这些菜编入了“名菜”一栏。编撰时划了成都、重庆两个片区。成都片区以成都市为中心,包括川西、川北,口味清淡一些;重庆片区以重庆市为中心,包括川东、川南,口味重一些。这也只是味道的差别,在味型上还是一致的。
其实,川菜在成都和重庆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重庆有一批师傅最早是从成都过去的,这批人主要属于“颐之时”。后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调到北京时,带了一部分人走。留在重庆的厨师的做法与成都基本相同,与一些重庆地方菜还不一样。所以,当时成都、重庆两地厨师的共识比较多,老龙门阵能摆到一起,一说起来都能接受。加上当时四川省蔬菜饮食公司很有权威,成都、重庆的饮食公司在行政上都归它管,两边的意见很容易统一。
经过长达四年的不懈努力,《川菜烹饪事典》于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半年内就加印了三次,共七万多册。作为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四川烹饪文化、饮食历史、烹调技艺和相关烹饪科学知识的工具书,《川菜烹饪事典》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在行业内外均受到广泛好评。
这本书的一大贡献,是首次明确规范了川菜的二十三种味型。以前沿袭的味型概念,只是在民间流行,由政府组织整理并正式发布,意义就大不一样了,也因此奠定了这部书的权威地位,为后来川菜的烹饪技术规范,以及教育、传承、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据我所知,对本菜系的味型进行梳理,这在全国还是首例,及至今天,其他菜系也没见到这么明确的味型概念。
《川菜烹饪事典》一经问世,便风行一时。不少厨师和管理者说,他们的厨房都是人手一本;凡是新参加工作的,厨师长都要求他到书店去买这本书;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无需上面要求,都把这本书看做是必备的参考书。20世纪90年代,川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餐饮业迅猛发展,从业人员越来越多,这本书的销量一直居高不下,国内其他菜系的从业者也非常武汉白癜风医院白癜风怎样快速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