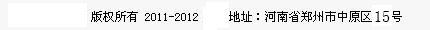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一位老先生来到顾颉刚的宿舍,后者大喜过望,与其相谈甚欢。过了些天,顾颉刚便迫不及待地约了丁山、郝昺衡一起去回访这位老先生,并拿出自己在泉州买的《柳洲诗话图》请他题字。没想到第二天,老先生便又把书送来,顺便告诉他,自己隔天就要回福州老家了。
听到这个消息,顾颉刚面露怅惘之色——这位大他27岁的陈衍先生,俨然已是他的“忘年之交”了。临别之际,竟颇为依依不舍。
陈衍,福州人,字叔伊,号石遗,晚称石遗老人,曾用笔名萧闲叟,以精深的诗学、儒学、经学、朴学、史学、经济学等综合造诣,在清末民国初文坛上享有盛誉。他早年幕游各地,年回闽之后,曾任《福建通志》总纂。年—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曾任国文系主任、国文正教授。
作为当时著名的诗论家,他论诗交友,教授学生,建树极丰,其诗友里包括周殿熏、黄瀚、虞愚、林尔嘉等在厦门名噪一时的人物。在他来厦大任教后的诗歌里,“横舍高楼壮海滨”一句,也成为当时人们对这所新建学校的经典评价之一。
厦门大学第一届学生叶国庆曾经在《我们那时候》一文中提到,当时的学校有一个诗社叫作“苔苓”,社员有三十多人,每学期会征集诗歌一到两次,出题的就是毛夷庚和陈遗石(陈衍)老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厦大校园(紫日供图)
但陈衍的另一个头衔,很多学生或许并不清楚。早在年,他便以萧闲叟的笔名编著过《家事科烹饪讲义》,在中国烹饪史上,首次将烹饪方法、菜谱编著成书,且正式成为国民教学的教材。
《家事科烹饪讲义》全书共三万多字,经教育部审定将其列为全国中、高级师范学校和女子中学必修课程的教材,并定名为《烹饪教科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年,经修改后取名《烹饪法》,到年共出版过三万册左右。
该书分作前编与后编两部分。前编的“总论”,由“绪言”“饭菜论(上)”“饭菜论(下)”“荤菜论”“素菜论”“锅灶及诸燃料”“刀砧及诸杂器”“盘碗”“作料”及“食品不能分时令”10篇组成;后编则是合计道菜式的做法,广涉猪、羊、鸡、鸭、鱼、虾及各类菜蔬做法,但都是日常家居菜品。书中更汇聚了烧、煮、炒、汆、蒸、炸、卤、烩、炖、溜、爆等烹饪技法,可谓包罗万象。
民国期间,坊间流传着多种私家菜谱,仅商务印书馆就出版有《陶母烹饪法》《俞氏空中烹饪》《英华烹饪学全书》《家事实习宝典》《家政万宝全书》《实用饮食学》等,唯有陈衍的《烹饪教科书》署有“教育部审定”,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烹饪教科书。
能写出这样级别的著作,可见陈衍本身一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
在《陈石遗集》的题解里,作者陈步有这样的描述:“陈衍治家勤俭,极富生活情趣,每以‘君子不必远庖厨’自况,以诗会友之馀,常亲自下厨作膳,以佳肴奉客。陈家菜在当时颇负盛名,闻说当时福建省主席陈仪即盛赞陈家菜较北京谭家菜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视本书为‘陈家菜谱’,亦无不可。”
说起来,陈衍还有一个忘年交,便是以《围城》蜚声文坛的钱锺书。
钱锺书非常敬佩陈衍的学识和人品,他曾写《论诗友诗绝句》称颂陈衍:“诗中疏凿别清浑,瘦硬通神骨可扪。其雨及时风肆好,匹园广大接随园。”诗中所说的“匹园”是陈衍的诗楼,而“随园”正是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住所。
钱锺书把匹园与随园相比,有一语双关之意,一是说陈衍的《石遗室诗话》正与袁枚的《随园诗话》相类;二是说两人都是知味之人,袁枚有《随园食单》流传后世,陈衍则有《烹饪教科书》为人们留下烹饪之大观。
自明清以至民国,中国的饮食文化从传统到兼容,蔚为大观。而作为标志性著作的这两部书,又各有千秋。例如,《烹饪教科书》的总论部分,有点类似袁枚《随园食单》的“须知单”。
但较之袁枚的观点,陈衍有些与其相结合,有些则与截然相反。如在“食物不能分时令”一节中,陈衍则明显相异于《随园食单》的“时令须知”。袁枚说“冬宜食牛羊,移之于夏,非其时也,夏宜食干腊,移之于冬,非其时也”,意为要尊重自然规律,所食不能非时。
陈衍则反其意,特别申明:“食品不能分时令,猪羊鸡鸭,四时皆有,不能强派定某时食猪、某时羊、某时食鸡、某时食鸭也。惟鱼与蔬菜,四时不同,有此时所有,为彼时所无者。然南北亦各不同,如南边鸡四时皆有,鸭则夏秋间新鸭方出,北边鸭四时皆有,鸡则夏季新鸡方出。故食品不能断定某为春季,某为夏季,某为秋季,某为冬季。只有预备多品,分门别类,以待随时随地酌用之耳。”
《烹饪法》里提到的素菜
除此之外,《烹饪教科书》也全然不同于一般的中国食谱中所谓“盐少许,酱油少许”的做法,都会言明“酱油一两,糖三钱”等,很具科学精神。
厦大校友、闽菜专家刘立身在其《闽菜史谈》中,特别表达了对陈衍与《烹饪教科书》:的看法,“陈衍的人生实际上跨清末与民国两时期,加之属名士之列,多有书载其美食之事”。
他还提到了清朝徐珂《清稗类钞》里记载的陈衍戏作《饮酒和陶》诗十章,以及陈衍晚年充满烟火气的诗:“晚菘渐渐如盘大,霜蟹刚刚一尺长。独有鲈鱼四鳃者,由来此物忌昂藏。”
既是一首有趣的好诗,又有满满的画面感,陈衍先生的饮食文化修为由此可见斑。他在厦大任教期间,也正是这所新兴的大学最具想象力的创业期,尽管从现有的文献中没有找到其与厦大餐饮的直接关联故事,但他所著的这本“国民教材”,影响深远,当年厦大的大厨们,或许多多少少都曾受益于此吧。
《鲁迅全集》里提到陈衍来厦门
(部分内容节选自《厦门大学餐饮百年》)
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