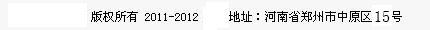江山信美,沃野丰盈。小留啖家三杯酒,试看新园几多樱。岁月之杯,自有岁月之赠。
本文作者罗亨长先生是川菜著名美食家
味在四川。四川乃天府之国,沃野千里,物甲天下,故有自贡咸、汉源麻、内江甜、保宁酸、威远辣的“五味之仓”之美誉。四川历经三次移民,引来了“下江”(指汉口、南京、上海)和京、津、粤、鲁乃至全国各地的名菜甚多,这样南北西东,荟萃撷英,对四川(主要是成都)私家菜和餐饮业来说,便必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内容。于是,川菜原料不断扩展,烹饪技艺越发多端,其味当然是无穷无尽的了。
闻香下马,知味停车
有滋有味的菜品方称得上佳肴。因为,滋是味之依,味乃滋之托。滋和味相互依托才产生美味。有一种味叫远味——泡菜坛应离厨房远些,以免受热变味;给食客煮赖汤元、龙抄手的炉灶应靠近就餐的食客,鲜香之味方可及时送达,这叫近味。
拌夫妻肺片等菜,厨师只淋调味汁,由食客互助自拌,这叫漏味(让调味汁慢慢漏在菜中、盘底),又叫初复合味。菜肴上加芫荽或葱丝或红灯笼海椒(鱼肴开门红)等等,这叫冠味,又叫盖味。煮汤放盐,这叫死味、硬味;如用榨菜或芽菜或酸青菜或泡萝卜煮汤,这叫活味、软味。
泡菜坛应离厨房远些,这叫远味
有一种味叫核味;即是说菜肴(食品)的每个部位都是同样的味。以红苕为例:红苕最内核之处都与其它部位有相同的甜之香味。没有核味的菜肴(食品),虽有外美,但无内秀,说明食材不达标或者厨艺不过硬。
味外之味,是指就餐之氛围、菜品之文化、服务之至美、价格之合理,没有此“四之”,再好吃的东西,只能叫食物——食之物也;有了这“四之”,则可称之为食品——食之品味也。
再高明的厨师也调不出食材本身的鲜美之味。因为这鲜美之味是天赋,不是人赋。与鲜美之味相对而言,有一种味叫陈味。陈味一般是指郫县豆瓣、老腊肉、酱肉、皮蛋、盐蛋、泡酸菜、豆腐乳、大头菜等。但,陈味不能过陈——应在其有益无害的发酵期内使用,一旦过陈,则不堪一吃矣!
盐为味之首。苏轼诗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他认为音乐固能给人以美感,但它不能令人忘却食物无盐之苦。杜甫说,火候到时味方甘。故食之美在于味甘。凡达“甘”标之食,一旦与它食“团结”在一块儿,便相互“借”、“夺”其味,从而互补生辉。“借”、“夺”合一而为“调”。菜肴经这么一“调”,其味巧出,谓之巧味。
味外之味,指就餐的氛围
无味之味乃至味
著名美食家车辐曾对笔者说:“戏曲中以善听者为知音,食道中以善吃者为知味。一经引为同好,则感到分外亲切。”于此,我想起了他早年摆给我听的“龙门阵”。他说,老成都名厨罗国荣,当年最尊重写“孩儿体”的大书法家谢无量。谢亦常以书法比喻罗国荣烹调的三款菜肴杰作——“开水白菜”、“口蘑肝膏汤”、“鸡皮冬笋汤”。谢评之曰:“这三道汤菜就好比三希堂法帖中的三件法宝。”后来,罗被贺龙元帅调北京饭店主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大师还常给谢老送去拿手好菜。谢老不愧为大艺术家,他不仅知味,而且知味外之味。这味外之味乃时尚所言附加值也。故上述三味,其价不菲!
余幼时,曾寄读郫县姑父家。姑父时任郫县“万担仓”总管兼福川银行总裁家厨。一日,总裁宴请国画大师张大千。大师对姑父的拿手菜“滑油肉片”倍加赞赏,而对“拌兔丁”却不屑举箸。大师说,拌兔肉易染病菌,难避草腥。兔肉含多种肉之营养,故名百味肉、美容肉,若以双椒(干海椒和花椒)滑熘焐之,再加“乱棒”(芹菜、蒜苗、芫荽、大葱之节)“棒”之,其味当可夺魁!姑父如法炮制,一举功成。
何谓无味之味?
无味之味就是无味之味,它恰似不假修饰的妙文、不施粉黛的淑女,其隽永寓于其中,就看你有没有品尝、咀嚼、审视这“无味之味”的舌觉、视觉和理学啦!无味之味乃至味,故难悟。
人情味天天都有,但愿大家天天碰到。要知道,不期而遇之味谓之“碰味”。的确,不期而遇的人情味最香、最妙!比如说,你一不小心“让青春撞了一下腰”,即是人情味。又比如说,你不经意间在吃回锅肉时吃到了一颗香豆豉,吃椒盐粽子时吃到了半粒好花椒,吃邮亭鲫鱼时吃到了一绺泡萝卜丝丝,反正你一下子便会感到某种异样的舒爽,这就叫“碰味”。
上好的老饕是讲究色香味俱全的
总而言之,味在麻辣之间、甜酸之间;味在冷热之间、软硬之间……味在两种不同的味觉和触觉之间。有时候,味在食客的想象之间。追根溯源,人世间所有之味,均在天地之间、山水之间;而山水之味则在山水之间。
吃锅圈子想起了“吴神仙”
雅安市西十里许,有镇多营。当年,发明馒头的蜀丞相诸葛亮,督军征战,连营于此,故名。世事沧桑,其营盘早已灰飞烟灭。如今,大道通衢,集市兴旺。
前不久,“雅安通”请吃于该镇。主人好客,不仅头菜双上,而且红白两味并举:油泼尖椒雅鱼和清蒸八宝雅鱼。此二菜我曾朵颐,所以仅有些许惊喜。唯一种叫锅圈子的面食,从未闻过也未吃过,故而特别钟爱,连续吃了三枚。
之后寻思,觉得似曾相识,推开记忆之窗,我想起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家住成都少城长顺上街之时,一位被街邻称为“吴神仙”(因为他打锅魁非常敬业,每道工序他都要带上徒弟亲自操作,于是他的头脸、衣裤、鞋袜都扑满面粉,状若白发仙翁)的“吴锅魁”来。
“吴神仙”打的白面锅魁与锅圈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先将面剂子放在案板上,经揉“熟”、擀平、盔圆三道工序之后,便放在抹了菜子油的平锅(鏊子)上,让它两面炕个半熟,便夹在平锅下的炭火炉的炉膛边烤起,时而翻翻面,使它腹背受火,形成“蜞蚂肚”时,才一个个夹出炉膛,摆在陈列锅魁的木梯板上出售。
“吴锅魁”就在我家斜对面,一出炉我便捷足先购,“天狗吃月”地咬它一口,那“蜞蚂肚”立马喷出热气。如果在冬天吃,双手如同捧了个“烘笼(儿)”,越吃越热和。“蜞蚂肚”不断喷出的热气,虽有点袭人,但它那本真的甜甜麦香,正是由此诱得你迫不及待地将“吴锅魁”吞个精光。
老外亦爱川味
老成都的叫卖声
举凡经商者,其商品欲要人们知道,从而接受购买之,都必须通过一种或数种媒介手段,才能达其目的。这规律,大小生意皆然。
当年,成都少城的小吃经营者,深谙此道,而且能因商品之异而异口不同其声、异器而不同其鸣。少城卖马蹄糕(又叫梆梆糕。马蹄糕因形而名,梆梆糕因声而名)者,不用口吆喝,而用一节楠竹片击打竹筒,使其发出“梆梆”之声,作为宣传媒介。
这不费口舌,很快传到人们的耳里之声,既清脆又能播远,效果极佳。当人们第一次听到“梆梆”之声时,或许有点诧异,那人在干什么?听惯不惊了,便知晓是推销马蹄糕的。时日一久,妇孺皆知,童叟明白。所以,在屋头玩耍的儿童,一听见此种声音,便条件反射,经准确判断后,嚷着父母掏钱去买那梆梆糕吃。
初夏,成都还不算炎热,近郊地里的玉麦和田埂上的黄豆便次第成熟了。一些知道抓住机遇的村嫂们,便来少城走街串巷,兜售“熟玉麦”和“毛豆角(儿)”了。她们穿的“对门襟”衣裳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光光生生;左手挽一个装有“熟玉麦”或“毛豆角(儿)”的船形竹篮,上面盖一张双层阴丹蓝布或洁白的厚毛巾,右手则是提杆小称,挨家挨户地小声唱了起来:“买玉麦,买熟玉麦,买热热的——熟玉麦!”接下来,另一个村嫂亦念念有词:“买毛豆角(儿),新鲜的毛豆角(儿),五香盐煮的毛豆角(儿)哦!”大约每隔两三间铺面,如此这般轮流、反复地吟唱着。
闻香下马,怀味隽永
这叫卖的声音令人愉悦,仿佛是从川西坝子那特有的林盘头,或从清清的堰河水边飘来的咏叹调,给初夏阳光照耀下的少城,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意。于是,少城更显得玲珑和妩媚了。
那时,我家住在长顺上街与东胜街交汇处,左侧有一棵高大的、绿荫覆盖的泡桐树。夏季,上午十一时左右,便有一个卖用红糖熬的糖水糖豆花,和调料齐全的麻辣豆花挑担停在那树下。卖豆花者姓李,眉宇间给人一种祥和之感。他身穿阴丹士林长衫,头缠漂白布帕子,与现在成都石磨豆花庄磨豆花的人打扮一模一样。
“李豆花”也不用吆喝。他的扁担后半截挂有一个只盛大半桶清水的小木桶。他把一副盛豆花的碗匙沉在桶底,将右手潜入水中“胎”起碗匙,用大拇指轻压匙柄,一抖一抖地——那多(儿)多(儿)多(儿)……的声音便响出水面。这声音的原理,类似《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所描写的桨橹从河水中一入一出的原理相似。所以,很独特,有韵味,有情趣,极易招徕食客。可以说,这声音是“李豆花”的同义语,等于“李豆花”,而不是王豆花、张豆花什么的,更不是马蹄糕。
少年好奇,我常去观察他摇碗匙的动作,细听那从小木桶中“升起”的含有浪波的委婉的“碗音”。但愿像李豆花类似的名小吃品牌和他们的“叫卖声”在成都重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川味亦在不断“变脸”
邱佛子豆花饭庄四大特色
过去,居家少城的小士绅们,一般起床较晚,也很少过问早饭,因大都在昨晚消夜时吃了各色各味各形食品,不仅腹中不空,且那“花肠子”蠕动较慢,尚需消却饱胀,故有的人则在自家门前的树阴下,品“一支烟”工夫的香茶,敦促自己“出恭”。待“轻松”之后,日头已爬上三竿,才想起“日课”来。于是,自个儿或临时组成AA制(当时称“盘子头开花”、“打平伙”),朝祠堂街东头的邱佛子豆花饭庄走去。
邱佛子的菜品,按今天的说法,属民俗乡土风味;菜鲜味正,不失典雅,一如川西农村少女般的美妙,令你回味久长,所以该店的客源甚广,除上述的一拨又一拨小士绅外,尚有右隔壁天府大戏院“新又新”川剧科班的演职员工,左隔壁“颐和园”茶楼的“学派”(当时在附近的石室、黄埔、蜀华、培英四个中学的同乡同学会的高中毕业生)茶客,本街坊“聚兴诚”银行和布疋百货商行的员工,在少城公园遛完鸟、练完晨操和打完太极拳的市民大众,以及刚从盐市口安乐市下市的商界人士……他们对邱佛子质好价廉且可口的饭菜,情有独钟,因而趋之若鹜。
邱佛子老板留有胡子,为啥不仿效当时“痣胡子”龙眼包子那样把店名起成邱胡子呢?因邱老板信佛,常去各大寺庙进香、吃豆花斋饭,便自诩为“佛”的弟子,故名。他对选料、磨浆、点卤、配味四大关键,了如指掌,固善能集各大小寺庙豆花之大成,这也因之顺理成章地成为邱佛子。
口舌生津
邱佛子四大特色之首:红油辣子豆花。此豆花的盛器乃兰花花高脚喇叭形碗,既有格调,又显豆花多,煞有卖相。此豆花名品,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被移植在西玉龙街陈麻婆豆腐店出售。豆花质味如初,但盛器却改为小碗,遗憾。
邱佛子的第二个特色是“冒儿头”饭。邱老板每次从双流县马家寺拜佛进香后回成都时,必带回数袋无稗子、牙口好、又涨饭、驰名川西的马家寺场上熟大米,吩咐专厨煮成沥米饭,在店堂现蒸现卖。那蒸饭方法实为古朴、科学:专厨将沥过、蒸至九成九熟的米饭,慢慢地“梭”入大铁蒸锅的竹篾子上后再蒸;同时用一根直径约10厘米的、打通关节的青翠竹筒,在竹篾子顶尖相应直径的孔中插入锅底,让蒸饭的水蒸气通将上来,专厨便观察冲出竹筒口的热气,来判断火力大小、锅底有无蒸水。如热气旺,则说明火力足,那青翠竹筒便会因振动发出“笃、笃、笃、笃”之声,这正是蒸饭最佳状态的反应。如热气不足,则说明火力不旺;如热气不上,则蒸水已无,俄顷,便有黑锅、饭之险。于是,专厨便会根据青翠竹筒冒出的“气相”来调整、防范、补救。
如此有情趣、有章法、有过程地蒸出来的“冒儿头”饭,立马端上桌来,最能引发食欲。食客用筷子一按,那“冒儿头”尖尖便“消失”了;舀上几勺鲜汤泡上,那松散的饭便“卧”在碗底了;端碗扒上几口,那饭便即刻被吃光了。——简而言之:“冒儿头”端来是尖碗,筷子一按是平碗,鲜汤一泡是浅碗,嘴巴一张是空碗。在当时,这四句话已成为少城厨界、食界的口头禅。虽说有点儿夸张,但却也很形象地道出了邱佛子的“冒儿头”好吃受吞。
邱佛子的第三个特色是“豌豆肥肠血旺汤”。此汤原料便宜,却因制作精细而提升为该店的主打汤菜。该汤汤宽质好;肥肠切细圈,鸭血切薄片,再加上经炒得粉香的豌豆入锅慢烹之后,用白瓷盆盛汤,汤上撒一层香葱花,再滴上数滴香油,此香油因汤之热气迅速扩散开去,呈现出上千个亮晶晶的小珍珠儿,与百来颗绿白相间的香葱花衬托成绚丽的图案;旋即上桌,诱得食客们口舌生津,欲吞不能——降温后才能吃。
邱佛子的第四个特色是小菜两碟:“椒油黄丝”和“翡翠青笋”。黄丝即大头菜丝,又名猴子肉丝——那大头菜原色原貌与猴子色貌相似,故名。黄丝切得均匀细长;海椒油、花椒油和盐(切忌豆油)有点意思地将原丝浸成嫩黄,且不沾一点儿水分,拈在白盘中颇有力度,仿佛是浓缩了的袖珍新枕木架。端起此菜视之,从“枕木”空隙中可见对面的图像。这黄丝麻辣香咸脆适度,下饭最宜。那“翡翠青笋”则是将嫩青笋的中段,切成10厘米见方的骰子状,早上泡入装有鱼辣子节的玻璃缸中,中午待客。
川菜是川人的一大日常艺术
食客扒一口泡有“豌豆肥肠血旺汤”的“冒儿头”饭,拈上一两颗翠色青笋和一节翡色鱼辣子,和着在口腔中嚼着,尔后,食客的舌蕾自然复合其味,此刻,顿感一种殊胜的美妙,流进了心田。所以,邱佛子的常客们,常在店堂现身说理:“好吃的东西不一定价贵;反之,价贵的东西不一定好吃。”这话正确与否,关键是经营者的美食理念正确与否,当然还包括厨师的识见、视野和厨艺如何。
如今,邱佛子其人已乘鹤西去,但老成都们一闭上眼睛浮想沉思,那招牌上的“邱佛子”三个金字,在闪闪发光;那店堂的火爆场面,仍历历在目……
“读懂我们的城市”——
欢迎订阅《读城》杂志,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原载/《读城》年11月生活美学
文/罗亨长图/邓平模邓楠主编/付强统筹/雍璐萍
设计/杨焰制作/马文佳
↙欢迎订阅《读城》杂志,点击下方“阅读全文”预览时标签不可点